服務熱線
13706606868

“我的名字叫李安,但是我很不安”
眾所周知,華人導演中,李安已經是大師級別,而最近他參加的一期訪談節目里,當主持人問他:您是一個很有安全感的人嗎?李安帶著他一貫儒雅的微笑回答:我的名字叫李安,但其實我內心很不安的。那一刻,他就像個孩子。

▲李安與弟弟李崗、父親李升、母親楊思莊
李安的父親是一所中學的校長,治家甚有古風、教子極為嚴格,甚至很長一段時間逢年過節在家里還要行跪拜禮。李安就是在這樣有濃厚中國氛圍的家庭中成長起來的,家庭帶給他的不僅是中國文化的浸染,也養成了他壓抑自卑的性格。
李安直言,從小到大,他和父親的交流都很少,大部分時間,都是在餐桌上面聽父親訓話,他則默默的聽著,不敢有任何回應和表達。

▲少年李安與父親
高中時候,李安曾努力學習,成績也很優秀,但是到了參加高考的時候,他就因為緊張而影響發揮,連續兩年都高考落榜,而作為這所學校校長的兒子,李安感到無地自容,對父親有著很深的愧疚。
在第二次復讀以后,李安因為數學成績的拖累,只勉強湊夠分數上了一所藝術大專學校,而他的父親從小就對他們說過:此生最痛恨的職業一是船員,二是演員。李安知道父親不認同他的選擇,但他還是在沉默里做著自己的堅持,這或許就是他對于父親無意識的叛逆。
很快,李安就從高考的陰影里走出來,融入到新的學習生活。他成了校內的積極分子和文藝骨干,還多次參加環島巡回公演,甚至到工廠里表演舞臺劇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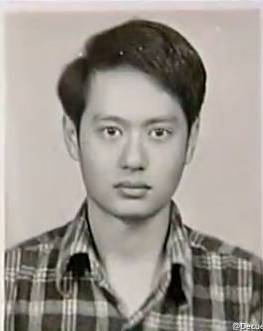
▲青年時的李安
但只要一回到家,李安就會收斂很多,因為害怕父親責怪自己。有一次因為自己黑瘦的形象,父親在飯桌上當場訓斥他:什么鬼樣子!已經接近成年的李安很尷尬,將碗筷一放,就直接回自己房間了。
這樣的沉默對抗,一度讓他們父子關系異常緊張。后來父親提出想讓他出國留學,希望他能拿到學位后回國當教授,李安沒有采納,堅持著自己做導演的夢想之路,如果說上藝校是李安的第一次叛逆,那執著的要走導演這條路,就是對父親的再一次叛逆。

▲堅持導演夢的李安
直到后來看他在美國連續拍了幾部反響不錯的片子,他的父親才逐漸認同他這個職業,并預言憑他的天賦可以在50歲左右拿到奧斯卡獎項。李安沒有辜負父親的重托,在46歲那年就提前拿到了奧斯卡獎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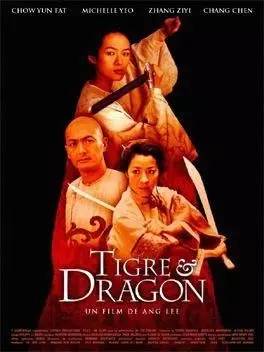
▲《臥虎藏龍》獲得1999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將
就在父子關系逐漸和緩的那些年,李安接連拍攝了“父親三部曲”來表達對父親深沉的敬畏和愛,這三部影片分別是“推手”,“喜宴”和“飲食男女”,影片中包含了中西文化的沖突,也有傳統的家庭倫理道德里兩代人觀念的沖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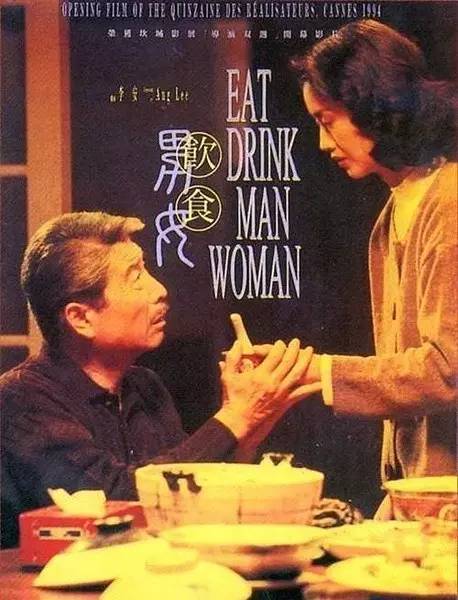
▲父親三部曲之《飲食男女》
而三部劇中無一例外的嚴厲權威的父親角色,都和李安現實中的父親有很多相近之處,李安自己直言不諱的說:自己是在電影里表達對父親的愧疚和敬意。
李安在49歲時,突然覺得自己江郎才盡,身心俱疲,他曾對父親表達了退隱之意。那時的父親年歲已老,性情柔和了很多,他沒有批評李安的草率決定,而是當即寫下一幅字以勉勵自己的兒子:入山不必太深,下筆不必太濃,頂起鋼盔繼續往前沖。

▲李安與父親
李安雖得父親得鼓勵,但當他接到斷背山的邀約時,還是在退休和拍片之間猶豫不決。而就在這時,李安接到了臺灣傳來的父親過世的噩耗。李安以長子身份迅速返臺,處理了父親的喪事。而后回到美國,來不及悲傷,就開始了斷背山的拍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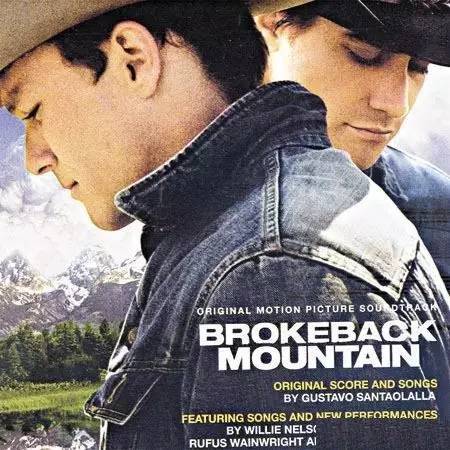
▲《斷背山》在第78屆奧斯卡金像獎中獲得八項提名,并奪得了最佳導演、最佳改編劇本與最佳電影配樂三項大獎。
“斷背山”里的Jakre也有個嚴厲的父親,和李安的父親一樣,對兒子有很高的要求和期待,Jake因此叛逆而很早離家,我相信這一段內容里隱含著李安對父親的懷念。

▲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第85屆奧斯卡獎頒獎禮上獲得了包括最佳導演、最佳視覺效果在內的四項獎項.
后來的“少年派的奇幻漂流”里,有一個情節是,男孩派在孤船上獨自面對風暴時,朝著呼嘯的海面大聲呼喊“爸媽,對不起,我沒能見你們最后一面”的這一幕,讓李安自己觸景生情,情緒崩潰。
少年派這部片子再度讓李安榮獲了奧斯卡最佳導演獎,但沒有父親的喝彩,李安仍舊感覺內心有一個缺。

▲功成名就的李安,卻很不安
但是即便他挑戰了無數高難度的電影,做成了很多貌似不能完成的事,在生活中,李安人仍然內向靦腆,敏感不安,究其原因,首先是童年在父親絕對權威之下的個性壓抑,以及成長過程中未順遂父親意愿而產生的愧疚。用他的話說,他一生的內心勾結都是和父親完成的。

▲一生的內心勾結都是和父親完成的
童年的李安,由于父親的強勢,他很少有表達的機會,也因此造成了他表面乖巧服從的性格。而在日后他選擇了電影這條路以后,他的情緒在電影里得到了完全的釋放,電影給了他抒發情緒的廣闊空間,他獲得了掌控世界的感覺,沒有權威與他對抗,電影就是他自己的王國。
有了這些做鋪墊,他所有拍攝的賦予挑戰的題材都能獲得大的成功就不難理解,用他的話來解釋就是:仿佛有另一個隱性的自己逼著我往不安全的地方走,我沒有退路,只有往前沖。

▲電影讓李安逐漸將內心的那個小孩釋放了出來
因此就有了集最難拍攝的題材三要素(水,虎,孩子)的“少年派的奇幻漂流”,和讓普通大眾很難接受的同性題材電影“喜宴”以及“斷背山”,這幾部片子都獲得了空前的成功,也讓影評人對李安有了這樣的評價:他通過少年派放出了自己內心的猛虎,也通過那部同性題材的電影找到了自己內心的斷背山。

▲李安新片《比利·林恩的中場戰事》
就連最近的一部新上映的電影,李安又領先全球,運用了最先進的3D技術,很多人懷疑他是在玩票,標新立異,但當主演林恩站在舞臺上,鏡頭對準他時,他淡藍色的眼睛里泛起的眼淚,以及他嘴角細微的不自在的笑,都讓人有近在眼前的真實感覺,對于這樣一個有關情緒題材的影片來說,這樣逼真的清晰度,無疑是驗證一個片子實力的最好助力。
對于這部片子的意義,李安說不是在宣揚反戰,也不是在講關于PTSD(創傷后應激障礙)的修護過程,他是講述經歷戰爭后的男孩成長的過程。
我有一種錯覺,或許林恩就是李安,李安就是林恩,他們都受過傷害,他們都曾不被理解,但是通過電影,他們找到了自己的歸屬和愛。

▲李安與兒子李淳,一場父子的傳承
TAG標簽:李安,內心勾結,父親,內心想法,內心世界